编辑推荐内容简介作者简介目录书摘插图讨论
不拘泥于传统的模式是这部人物传记最吸引人的地方。约翰·曼饱含深情,亲自探访了史上许多事件的发生地,对他所描绘的人与事赋予了真实的血脉,仿若那近800年前所发生的故事不再是传说——我们感同身受,与那些剽悍的蒙古人一起呼吸、战斗,信马由缰,纵横沙场。
作者笔下的忽必烈没有被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光芒所掩盖,相反,这位大汗让这个骁勇善战的血统更加血脉贲张,他留下的遗产就是一个扩大的和统一的中国。
正是有关忽必烈财富的传说,以及东方的神秘色彩,在他逝世后的两个世纪,引发了哥伦布那次向西方的伟大航行,否则,发现美洲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约翰·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成吉思汗生死与复活》、《忽必烈汗》、《戈壁:沙漠觅踪》、《公元1000年地图集》、《阿尔法、贝塔》、《古腾堡革命》、《阿提拉》。
序言成吉思汗之孙
第一部春
第一章母狮及其子
第二章恐怖的第一战
第三章夺取云南
第四章龙居潜邸
第五章汗位争夺者
第二部夏
第一章新首都
第二章拥抱佛教与西藏
第三章征服的关键
第四章世界的主宰
第三部秋
第一章东征日本
第二章来自心脏地区的挑战
第三章大汗的新统治
第四部冬
第一章神风
第二章金钱、疯狂与谋杀
第三章扩张的极限
第四章东风西渐
第五章圣山,神秘的墓葬
参考书目
鸣谢
第一部 春
第一章 母狮及其子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唆鲁禾帖尼的第一缕幸运的曙光来自于成吉思汗1227年的去世。成吉思汗曾下令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他的汗位,同时他的所有4个儿子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行使个人的权力。年纪最长的术赤得到了今日的俄罗斯,其领地从西伯利亚中部延伸至黑海,但他却先于成吉思汗去世,其子斡儿答和拔都继承了他的领地。中亚从咸海至西藏分给了察合台。窝阔台的个人领地是西夏(基本上说,是中国西部的大多数地区)以及中国北部。最小的儿子拖雷则根据传统继承了其父的“炉灶”地区,亦即整个蒙古。这就是在适当时机将给唆鲁禾帖尼以权力的基础。
这样的分封包含着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边界依旧很模糊,而且依然有许多由当地人引起的争端。中国的北部仅被征服了一半,花剌子模仍然需要平定,俄罗斯的王公们虽然被击败了一次,但还会卷土重来。拖雷的地位是最为稳固的,因为他可以号令有现成的公职人员团队的本土。此外——由于牧人们可谓亦兵亦民——他在理论上就可能已经控制了军队。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种他并未去探究的可能性,因为他不但臣服于窝阔台而且还乐此不疲:兄弟俩都非常喜欢对方。既然没有来自拖雷的挑战,唆鲁禾帖尼自然也没有理由来梦想其儿子们的荣耀了。
窝阔台以一阵追随其父梦想的军事行动的风暴开始了他的统治期,发动了四次规模庞大而又彼此独立的战役。其一便是重新确立蒙古人在伊朗的统治,把它从其塞尔柱统治者手中夺了过来。对高丽的入侵则开始了一次直到1260年才宣告结束的征服行动。1231年又返回了中国的北部,这已经是成吉思汗逝世时最接近实现的目标。蒙古人兵分三路,分别由成吉思汗最伟大的独眼将军速不台、窝阔台自己以及拖雷来统领,而拖雷在20年前的第一次入侵时就已经征服了数座城市。
唆鲁禾帖尼的第二个意外之运是,在进入中国的战役初期其丈夫的去世。《秘史》以一种精心编造的戏剧化手法讲述了他的死亡:一个兄弟对兄长、将军对皇帝的忠诚的故事。1231年的战役开始不久后,窝阔台便身患疾病。水陆诸神都对他十分愤怒——很可能是震颤性谵妄,一种终身酗酒的结果。萨满们挤作一团来占卜病因。在检查完被屠杀的动物的内脏后,他们宣称需要一个牺牲品。但是在萨满们收集起战俘、黄金、白银、牲畜和食物来献祭时,窝阔台的病情却更加严重。现在能做点什么呢?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大汗的家庭成员可以替代他吗?拖雷此刻恰好在场,而且自愿做窝阔台的替身。但是该怎样办呢?萨满们又聚在了一起,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拖雷将不得不喝下某种可以把窝阔台的疾病引到他身上的毒酒。拖雷同意说:“巫师你来诅咒吧!”他所不知的是,窝阔台不仅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而且还要承受一种伤逝的剧痛,那是一个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的重负。拖雷喝了下去,毒药很快就见效了。在他还可以说话之时,他仅仅有时间把他的家庭托付给窝阔台来照料。“我还说什么呢?”他含糊不清地说道,“我已经醉了。”说完话他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且死去了。用《秘史》的非常唐突的话说,“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也许是这样,或者他也有可能死于饮酒过量。由于失去兄弟而心烦意乱的窝阔台再也没有恢复健康,悲伤成了饮酒量更大的借口,尽管如此,他还是又活了10年。
作为拖雷之遗孀,处在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中心的唆鲁禾帖尼翻开了新的篇章。对于一个富有的男人的寡妇来说,管理其亡夫的领地直到其最年长的孩子可以自行管理为止是蒙古社会的一个传统。当这件事发生时,她的长子蒙哥已经21岁了,但是窝阔台仍然给了她长久的管理拖雷领地的权力:她的家庭、她自己的一支军队、一个秘书处以及当地的人口,“所有的一切都要由她的命令与禁止、她的放任与约束来控制,不许违背她的命令”。本质上说,唆鲁禾帖尼变成了蒙古的女王,尽管还臣服于她的皇帝。
命运已经使她变得非常独立,而年届四十的她也有足够的明智与野心来保持这种独立性。当窝阔台建议她嫁给他的儿子(也是她的侄儿)贵由时——一个将会把两个主要的家庭连接在一起的联盟——她谦恭地加以回绝,并且说她的主要责任就是抚养她自己的儿子们。她终身没有再婚。在接下来的15年中,她治理有方,为自己赢得了无可辩驳的智慧与坚定的声望。来自局外人的报告都对此一致赞同。“在鞑靼人中,除了皇帝的母亲,这个女人是最为著名的。”教皇的特使之一约翰•普拉诺•卡尔平尼写道。“极为聪明和能干,”拉施特说,并且进一步赞扬她“能力极强,十分智慧与敏锐并且对事情的结果考虑周全”。“所有的王公都对她的管理能力惊羡不已。”一位希伯来医生巴尔•赫伯留斯说,而且他还加上了一节引文:“如果我在女流之辈中看到另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应该说女流之辈远胜于男人。”
她的机智在其抚育4个儿子的方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她保证他们都受到传统的蒙古方式的良好教育并熟知成吉思汗的札撒。但是这个帝国十分宽广,有着许多信仰。她从她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一一个克烈人和基督徒嫁给了一个蒙古的萨满教徒一不疏远盟友和臣民有多么重要。所以她的家庭里就有了佛教、聂思脱里教以及儒教的家庭教师,而后来在为儿子们挑选妻子时,唆鲁禾帖尼也以自己的形象为根据——自信、精力充沛、聪明、不墨守成规并且十分独立,并因而也带有了曾是成吉思汗更为令人惊异的特质之一的容忍。长子蒙哥选择了依然做一个萨满教徒,但却娶了一个聂思脱里教徒;旭烈兀,伊斯兰波斯后来的统治者,也娶了一位聂思脱里教徒为妻。忽必烈将要娶好几个妻子,但与其终身相伴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察必,一位著名的美人和热情的佛教徒。
与帝国成长相伴随的是财富的源源不断的流入。金都开封于1233年的陷落,迫使金朝皇帝逃亡(他被围困在了宋朝边界的附近并被迫自杀)。在成吉思汗首次入侵20年后,整个中国北部都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1236-1242年,西方的战事使得蒙古人的控制区越过俄罗斯的草原扩展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本土,窝阔台继续着由成吉思汗开始的建立一个完善的帝国管理基础的进程:制定成文法律,进行人口调查,并增加了税收的流人。
窝阔台现在也已经看到了成吉思汗曾经看到的一切:这就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帝国不能够以营地来进行统治。他需要一个首都,一个蒙古人在克鲁伦河畔阿布拉格旧基地的替代物。这个仍然有待于详细的考古调查的地方,坐落在原始的蒙古人中心地区的南缘,肯特山就是在这里渐变为草原的。它的北面是大山、森林和安全的避难所;而它的南面则是草原、戈壁以及作为贸易与战利品之源的中国。对于一个部落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总部,但并不适于一个帝国。成吉思汗知道一个可以从那里管理他的新建国家的最好地方。它坐落于更加遥远的西方,在鄂尔浑河的河谷,这里是前突厥帝国的统治中心。突厥人称其为哈喇和林,意为“黑色砾石”。成吉思汗曾于1220年将它选作了新都,但此后却无暇进行建设。窝阔台于1228年在阿布拉格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忽里台,并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他的统治期,也极有可能是在这里,他监督了收入《蒙古秘史》中的传奇故事与信息的收集,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也正是他再一次实现了其父的梦想,于1235年开始把哈喇和林变成一个永久的定居点,而这一切则是在刚刚完成对中国北方的征服之后、下一次大规模的西征之前。
这是一个有四个大门的土墙围绕的小镇,里面有一座宫殿,地板是木制的,有木头的支柱和盖着瓦的屋顶,附近的地窖则用来储藏财宝——近来的发掘找到了一些雕像和有佛祖头像的陶俑。与此相连接的是一些私宅,前面则是一座背上驮有浮雕石柱的巨型石龟,与那些通常守卫中国寺庙的石龟一样——也许这只石龟仍然还在孤独地为哈喇和林的替代物额尔德尼召值守夜班。在里面,一条中间的过道直通台阶,其上便是窝阔台的御座。当然,蒙古人从来都不建造城市——现在也依然如此:正如每个到乌兰巴托的访客将会告诉你的那样,这个地方的魅力来自人而不是建筑物。所以,哈喇和林也肯定曾经是这样的。不久,三分之一的城镇便被控制着供奉、萨满、商人、驿站邮政系统、财政以及军械库的政府机构占据。但是甚至在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工匠蜂拥挤进城墙内时,它也不完全是个城镇。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不鲁克曾在1253-1254年间见到过它,而且印象不佳:“你应该知道那个大汗的宫殿一文不值,它无法和圣丹尼斯相提并论,圣丹尼斯的寺院也要比那个宫殿强10倍。”
但这无关紧要:它是一个在此前从未有过中心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中心,这里聚集了成百的蒙古包(蒙古语称其为:格勒)、成千的大车和上万的牲畜。大批富裕的蒙古人,每人都有了需要由多达200头牛来牵引的为数众多的车辆,这些大车连成了一个由20-30辆大车队组成的巨大的车流,它们都在一辆由一位妇女驾驭的大车的带领下,排成一线缓慢而笨重地穿过开阔的草原。也许某个访客已经见过了一辆这样的巨型大车,它有10米见方,车轴像桅杆,由22头牛牵引,其上则安放着皇帝的大帐。有些人怀疑这样的大车是否存在过,但在今日的乌兰巴托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复制品,而其中的一个在每年7月的国庆庆典上,都会环绕体育场缓缓驶过。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笨重的怪物怎样或在什么地方曾被使用过,但在13世纪30年代,它无疑应该吱嘎作响地来往于旧的阿布拉格和新的哈喇和林之间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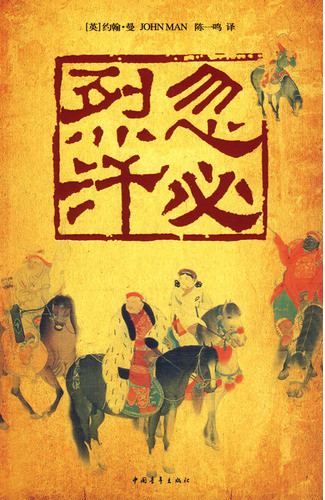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70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704号